
疏文:增结者,《净名经》云,有二比丘犯根本戒,发露求忏,优波离为依律定罪,疑心不释,净名言:“汝毋以常法扰乱其心,重增此二比丘罪。”永嘉拟之萤光,谓不能开其迷暗,而反增益之也,明卑之则机深教浅故。《弥陀疏钞》
此段疏文是叙说第二类情形:卑浅的法门,对根机深厚者不唯不得其益,反被扰乱心性,茫然失措。兹引《维摩诘经》二比丘犯重戒的公案。有二比丘结伴住阿兰若寂静处,一比丘入聚落托钵乞食,一比丘在寮房散心露形而卧,被一采薪女瞧见,生起淫欲心,盗行不净行,事毕撒花而去。比丘卧觉,疑犯淫戒,向同伴比丘叙说。此托钵比丘,瞋恨此采薪女,便追赶欲打。此女恐怖疾逃,堕坑而死。此比丘心疑惧犯杀戒。二比丘自觉羞耻,不敢问佛,便向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发露求忏,咨问决疑,希望得以免除淫杀罪咎。
优波离便依据声闻戒律,解说此二比丘罪过的轻重,告诉他们哪些罪轻可以忏除,哪些罪重不可忏除。时二比丘听闻,疑惧之心未能释除,并生后悔出家之心。
时维摩诘谏言:“尊敬的优波离尊者啊,你不要以寻常悔罪法扰乱其心,再增加这二比丘的罪咎了。应当直接除掉他们疑悔恐惧的罪恶感。所以者何?罪业没有实在的体性,乃因缘所生,不在内(六根),不在外(六尘),也不在中间(六识),十八界中觅其罪福,了不可得。一切诸法皆因我们内心的虚妄之见而有,其实如梦中所见一样,醒后即空。也如阳焰(春日旷野蒸发的雾气),远看似水,近看则无。又如水中之月,如镜中之像,全不是真实的,都是由妄心之镜所映现的,是从心里的妄想所生。若能了悟此理,令心安住于诸法的清净实相,才称得上是如法奉持如来所制定的律行。若能如是了知,才是善解如来宣说律法的真实义。”
时二比丘,闻维摩诘所说大乘实相忏,疑惧与忧悔之心顿然息除,豁然开朗,发无上菩提心,并发愿说:“愿一切众生,都得到维摩诘大士这样的无碍辩才。”证知,优波离奉小乘“律仪戒”,不能解除二比丘的疑悔。维摩诘奉大乘“慧解脱戒”,二比丘乃大乘根机,一闻便悟,淫杀二罪之疑悔,顿然消除。所谓“罪从心起将心忏,心若空时罪亦灭。”不但罪灭,无上菩提心亦发。
唐永嘉玄觉禅师(665—713年),早年修学天台止观,后参访六祖慧能大师,于某夜开悟得证,作《证道歌》,其中偈云:“只知犯重障菩提,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二比丘犯淫杀,波离萤光增罪结。维摩大士顿除疑,犹如赫日销霜雪。”意谓一般人只知道犯了重戒会障碍菩提,却不知道摩诃衍中,如来还有甚深微妙的秘诀——实相忏法。这两个比丘误犯淫戒与杀戒(并无犯戒动机),优波离按照声闻戒从事相上来结罪,如同萤火虫的光亮,不能开解此二比丘的疑惧迷暗,反而重增二比丘疑悔罪结(疑佛戒律过严,后悔出家),此则是“重增其罪”。维摩诘大士用大乘圆教实相忏法,顿然释除二比丘的疑惧之心,犹如赫奕日光消融霜雪一样。
又《证道歌》偈云:“勇施犯重悟无生,早时成佛于今在。”佛陀在世的时候,有一勇施比丘犯了根本戒,他即把三衣挂在锡杖上,高声唱言:“我犯重罪,谁为我忏?”至一尊者精舍前,此圣僧尊者针砭:“推罪性,了不可得。”勇施比丘言下豁然大悟,即往西方世界成等正觉,号曰宝月如来。可见对大乘圆机行人套用浅法,不能应机化导。唯圆顿机法相应,方得实益。此优波离“萤光增结”公案,正是阐明卑浅之法对根机深厚者,犹如隔靴搔痒,法不应机,效果适得其反。

















 净界法师
净界法师 智者大师
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
印光大师 慧律法师
慧律法师 善导大师
善导大师 莲池大师
莲池大师 广钦老和尚
广钦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
虚云老和尚 圆瑛法师
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
来果老和尚 道证法师
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
蕅益大师 宏海法师
宏海法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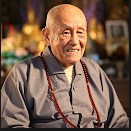 梦参老和尚
梦参老和尚 玄奘大师
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
大安法师